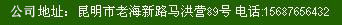|
这一周,《1/7》的摄制组去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见到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为精神障碍患者,长期生活在充满铁栏杆的治疗机构中,有家不能回。其实,你可能有所不知,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即便通过治疗可以出院,医院的大门。家人不愿接、经济窘迫、社区缺乏健全的康复服务体系等等,都成为他们“回家难”的重要原因。采访中,给出镜记者刘凝最大的感触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哀伤的故事,而他们的回家之路,除了有赖个体的家庭之外,还需要这座城市精神卫生的相关配套和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 —————————————————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哀伤的故事” 作者:《1/7》出镜记者刘凝 他,抱起那把蓝色吉他,弹唱:“请别对我说再见,我的心跟你一起走,无论天涯还是海角。”因为爱情,这位曾经的歌手,疯了。 她,白发苍苍,面带慈容。文革中参加了厂里的“保皇派”。斗争的复杂性,让这位年轻纺织女工,疯了。 他,在父亲得癌症后,学习气功,以期能给父亲治病。父亲去世的那一刻,他疯了。 …… 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位,都有哀伤的故事。 更哀伤的是,精神病复发率高,极难治愈。也正如此,精神障碍患者占据中国疾病总负担的首位。但他们更是家庭的负担和痛楚。长期的药费、住院费,是经济负担。病耻感带来的是深深的自卑情绪。 负重而行之难,难以想象。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家庭成员,让不幸成为这些家庭的统一代码。 那么,这个群体有多少? ——全国精神障碍患者万。 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话,这就意味每个人里就有一个。 与这个庞大的数字对应的是贫瘠。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国外,精神障碍患者一旦符合出院标准,就可以回家。迎接他们的还有与家同等重要的社区康复机构。那里有适合他们康复的环境和课程,还有爱心满满的专业人士、志愿者提供的不中断的服务。上海也有类似中途驿站的机构,也算全覆盖了,但实施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机构最渴望的专业人士支持、志愿者参与、企业赞助等缺口巨大。 上海做为全国首个给精神卫生立法的城市,在该法实施十二年后,将文字法律变成了现实法律,然而依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健全服务体系,说到底,竟然也是跟我们有关的,每个人也有不少事可为。 采访中,在阳光心园,我问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将来怎么办? 他说,现在啃老,他们死了,我就自杀。 听这话,不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所言。 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静默不言。 工作人员告诉我,她正在谈恋爱,和一个健全人。 不过,就是这样的好消息,也让人很难高兴起来。 《1/7》记者刘凝 精神障碍患者的归宿,不应是精神病院,融入社会,享受家庭的温暖,是他们的权利,也是社会的责任。如何他们的回家之路不再遥远?请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小七预告马少骅我演邓小平
- 下一篇文章: 为智力障碍儿子举办12场演唱会她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