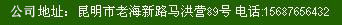|
80年前的今天,年10月18日,鲁迅的肺病再次猛烈发作,第二天病逝。 鲁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早已成为一个符号。人们记得《三味书屋》《祝福》《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以一种“标准答案”的姿态。他一度被树立成“纪念碑”,现在渐渐成为一块蒙灰的“牌位”。 陈丹青谈鲁迅多矣,今天分享他在浙大“纪念鲁迅诞辰年”的演讲。我们今天如何阅读鲁迅?又该如何认识他?或许丹青老师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维度。 是为念。 中国现代文化与鲁迅 陈丹青 文 选自《草草集》,本文有删节 今天又给令飞兄拉来这里,讲鲁迅。每次见到令飞,我很难装作不知道他的祖父是鲁迅,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海婴先生。海婴先生与我父亲几乎同龄,对我慈霭。周家的邀请,我很难拒绝。 当然,我愿意继续讲,还有别的理由。 1. 大家知道,D不再利用鲁迅了。譬如说,今年是鲁迅诞辰周年,换在早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鲁迅纪念日,绝对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令飞过问;举办地点在哪里呢:北京人民大会堂。台上的鲁迅像,和毛泽东像一样大小,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首脑,茅盾周扬等文艺高官,坐在台上,底下的听众又哪里轮得到诸位市民,必定是大小党官。我在七讲鲁迅的集子里特别选了四幅官方会场的新闻照片,其中一幅,就是摄于江泽民时代的鲁迅纪念会。 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中共中央,各级省市,不再举办鲁迅纪念了。诸位记得哪位中央官员,哪份政府文本,再来郑重其事提鲁迅吗?不提了。很好,鲁迅话题总算回到民间,至少,回到一小撮书生那里。九十年代中,王朔率先质疑鲁迅,引发争论—换在七十年代,就是现行反革命,负责刊发的编辑,至少开除党籍—但没有一位在职党官出面表态,说明什么呢,说明鲁迅的政治化,总算收场了。 这几年,鲁迅的部分文章也从中学课本里拿掉了,这件事,也有争议,但是官方不吱声。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认的:其中有一层意思不好明说,就是,希望九〇后,一〇后,此后的小孩子,顶好忘掉鲁迅,别学鲁迅,和谐社会顶顶要紧的一件事:大家闭嘴,大家学乖。 可是今天有头脑的年轻人,这些花招看得很清楚。此刻在座有一位复旦中文系的学生,八〇后,好年轻,我把讲稿事先请他提意见,他对神化鲁迅说了这样几句精彩的话,他说: 以尊敬鲁迅的方式,亵渎他,以传播鲁迅的方式,毁灭他,以利用鲁迅的方式,驱逐他。 说得多么好呢!我真为年轻人高兴。 2. 最近我谈论鲁迅的合集刚出版,拿到样书后,觉得仍然是在凸显鲁迅的孤立。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不出哪个现代国家曾经将本国百年的重要人物,删除到只剩一个人—虽然鲁迅如今也被悄悄删除了—不能小看这种孤立的后果,大家专门坐在这里纪念鲁迅,虽不是官办,恐怕仍在孤立鲁迅的老路上走。大家想想看,今天,多少民国人物的后代,譬如袁世凯、梁启超、章太炎的后代,譬如胡适、陈独秀、晏阳初的后代,还有张元济、邵飘萍、史量才的后代……根本不可能发起哪怕一小撮公众的纪念。除了极少数学者,大部分读书人,尤其是公众,对这些人物有感知、有记忆、有兴趣吗?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牛津版 这些人都是现代中国的影响者,有几位还影响过鲁迅。可是在历史荒原中,几代中国人不管读没读过鲁迅,不管对鲁迅了解不了解,仍会催眠似的念叨鲁迅、鲁迅、鲁迅……我更换过几个手机,只要打出“鲁”字,字码格立刻蹦出“迅”字,其他人物在字库中哪有这等待遇;令飞兄做了统计,过去三十年,多少学校、街道的名称,多少饭店、老酒、豆腐干的商标……都在政党的利用退出后,一拥而上,继续利用鲁迅的大名,登记,注册,赚钞票。 这就是鲁迅的孤立,孤立到只能被政治或商业轮番利用;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伟大到鲁迅的孙子要来大叫一声:鲁迅是谁?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尽可能将鲁迅置于民国背景中,再度辨认他,同时,将鲁迅话题穿越时间,拉到今天的语境,辨认我们。 我试图强调,除了鲁迅遗产,还有一份鲁迅身后的遗产,在这份遗产的时间表中,所有和鲁迅有关的事,鲁迅不知道,我们知道。 3. 这次令飞兄要我发挥的讲题,是“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这个题目太大了,任何现代中国的大人物,很难单独对应。……若是将话题改成“中国现代文化与鲁迅”,再把“现代文化”缩小到人文领域,焦距或许准确一点,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鲁迅,也会发生对应的困难。 譬如,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大转型的重要命题,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白话文运动、推行大众语、开办新学、介绍西洋思想和文艺、创作现代小说,等等等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庞大实践不论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莫不受到以上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如果这些影响果然构建了现代中国,鲁迅不会自居首功,如果给现代中国带来后患,鲁迅不该负其全责。一百多年来,是好几代不同主张不同派别的文人和党人,共同熔铸了所谓中国现代文化,鲁迅是其中之一,当然,是绝顶重要的一位。 鲁迅被孤立,造成几代人的误解,以为这些事情都是鲁迅一个人在担当,其他历史人物不过是反派或陪衬,很次要。如今史料告诉我们,攻击儒学,改造国民性,是五四激进文人的群体意识;白话文的缘起则早在十九世纪末,主事者是清末的传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话文运动,则是年左右胡适梅光迪等留美学生在校园内的书生论争,年才由本土革命家陈独秀等发起语言革命,日后推行大众语,是这场革命的题中之义和极端延伸。至于开办新学,介绍西洋知识,也都起于清末,清廷废除科举,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国家明令,同期的启蒙人物,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等,白话文运动攻击的林纾等人,早就翻译一百多种西洋著作,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了包括少年鲁迅在内的一整代晚清知识分子。在时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动手译介西洋小说的文人。 所以鲁迅顶重要的贡献,是开手创作现代小说的第一人。同期与后起的作家,不论服不服,大致公推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者,后来的文学虽有拓展,论到开创性、前卫性、深刻度、影响力,也没有哪一位人物超过鲁迅。 4. 评价鲁迅的难点,在文学之外,涉及远为复杂的历史情境和政治立场。譬如抨击军阀统治、揭露民国黑暗等等反对强权的呼喊,并非仅只是鲁迅早期中期的作为,也是当时一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而学习唯物主义、思想左倾,加入左联,暗通共产党等等等等,是鲁迅晚期的政治选择,这一选择,在三十年代引来中右翼的非议,五十到八十年代,被执政党高度宣扬、不容置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鲁迅当年的左倾,再度引来非议。 但这次非议和三十年代完全不同了。怎样不同呢,因为在那份鲁迅身后的遗产里,被劫持的鲁迅成为“D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虽然我们的时代抹着形形色色的伪文化涂料,唯“D文化”,才是所谓“中国当代文化”的核心。此外,诸位如果同意,除了各种各样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别称、变种、冒牌,我看不出什么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当代文化”。 现在退回鲁迅逝世的年之前,我们看见,鲁迅和左联青年在开会。我要说,他让自己坐在那里,既是当年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又是鲁迅个人未完成的选择。而三十年代的左翼革命,也正当未完成的时间段——当时的延安政府绝对不知道十多年后能够统治全中国,所以他们在窑洞里对上海一位著名前辈的道义同情,感动得要命;住在虹口的鲁迅呢,既不清楚延安和莫斯科究竟发生什么,也根本想不到他曾经热爱的中华民国将会崩解,尤其是,他想不到自己将要去世,不可能对他的选择,再作选择。 在最后的岁月,鲁迅读了几本唯物主义的书,开了几次左翼的会,和一些人要好,和一些人绝交,刚刚有了一个男孩,几位好友却被枪毙——总之,这样一个在年终止生命的文人,哪里想到身后成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方那尊巨大的肖像,哪里想到现代中国的焚书坑儒时期,他的书成为唯一的官方读本,哪里想到他的学生后来彼此揭发、彼此株连,又哪里想到当年支使他、欺负他的小青年周扬之类日后给投入监狱的罪名之一,竟是他三十年代私信中的几句话。 鲁迅,年 但我这样揣测鲁迅,仍是看轻了他。他早就预见、早就说过:革命成功了,诗人们就给碰死在革命的纪念碑上,只是鲁迅的方式最离奇,就是,他自己被弄成一个纪念碑。 5. 诸位同意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化,换句话说,就是D文化。它和欧洲、印度、日本、美国的当代文化,都不一样—和苏联的现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没听说斯大林借用托尔斯泰的片言只语,致人死命,或者,禁绝旧俄文学,命令所有苏联人只读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难想象,在这份中国现代文化中,鲁迅直接代表权力,绝对不可触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鲁迅”二字不再指一位作家,“文革”期间,政党以鲁迅的名义向国家官员开具逮捕证,并以鲁迅的词语宣布罪名。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称谓早已是政治名词,华国锋政府批捕张春桥的舆论宣传,就是所有报刊头版发布鲁迅三十年代指说狄克(即张春桥)的杂文。 是的。生前的鲁迅以他的犀利,招人忌恨,死后的鲁迅,招人恐惧。一个年后的文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面对毛泽东的同时,等于面对鲁迅。就我所知,不少鲁迅同代的大作家后代,目击父辈受尽屈辱,日后未必敢于公开怨恨毛泽东,却难抑制对鲁迅的怨恨。在一个纪录片中,我看见几位文学巨头的后代相聚了—包括海婴先生—我注意到,有一两位后代的发言与表情,藏着对毛的恐惧记忆,而流露为对鲁迅难以言表的忌讳。 所以鲁迅和“中国当代文化”的“关系”,还有一份迄今未便谈论的大题目,就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关系。这应该是鲁迅研究的深度课题,但我没有能力展开——我不知道尼采瓦格纳身后被希特勒利用、托尔斯泰身后被列宁利用,有没有专门研究;伟大历史人物的被利用,史不绝书,大家以为那样的时代过去了吗?从未中止。眼下,孔夫子巨大的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门竖起来,既不交代设置理由,也不上演宣传花招,好像很低调,其实蓄意而粗暴,暧昧而突兀,哪里是尊敬孔子,还不是为了政权。这份居心,鲁迅早就说穿过:“孔夫子,是被历来的权势者捧起来的。” 很抱歉,令飞兄,我对“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错了。如果“中国现代文化”指的是国家地位与经济成就,不必请出鲁迅的名字。我看不出鲁迅和这种文化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只能确认一点:鲁迅是个失败者。不单他,他的前辈如梁启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辈如胡适之或陈独秀,他的论敌如陈源或梁实秋,都是失败者—大家稍微想想:眼下的中国,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为之启蒙,为之奔走的中国吗?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局部,画面上五位学术大师左起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6. 从来有一句风凉话,说:鲁迅就知道骂人,没给国家民族提出建设性意见。这类D文化的变调、帮腔,不值一顾。倒有另一位失败到毫无利用价值的历史人物,胡兰成,这样子评价鲁迅,他在四十年代论及五四文学,曾经说:“鲁迅一生的功绩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鲁迅的真价值,“在于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什么叫做“否定”?什么叫做“叛徒”?在我们的时代,这两个词语就是严重的否定—今天绝大部分书生,顶顶忌讳说出否定的话语,顶顶害怕当个社会的叛徒—鲁迅神话给几代人的庞大错觉:他绝对正确,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最近去世的文学家史铁生有篇早期小说,写一群破胡同里的生产组工人闲谈鲁迅,完全把鲁迅看成中央首长,出入坐的是红旗牌轿车。工人们是对的,那位在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中央首长,就是鲁迅。 胡兰成的评价也是对的,简单,准确,说这句话时,鲁迅去世才几年。我唯愿将“叛徒”改成“异端”,因为叛徒一词被意识形态用坏了,民国初年,“叛徒”意指“异端”,很流行,鲁迅就有一条短语,说是中国有几种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抚哭叛徒的吊客”。此话有深意。谁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呢?可以开一份名单;谁是吊客呢?难说。胡兰成这个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愿意听听他的意思吗?我愿意听,因为他没有历史的名分,因为他不正确,因为他是彻底的失败者——在历来与当今的成功者那里,我从来不期待听到对于鲁迅的公正的评价。 7. 现在,我们略微回顾鲁迅的形迹和言说,看看他怎样的是个否定者,怎样的是个终生的异端。 鲁迅从未跻身于成功的集团,或试图成功的人群,用现在的话说,他远离权力。早年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结果辞职;以他位居第一的文学资望,大可稳做名教授,可是辗转几所大学,一律以辞职告终;他与英美派向来隔膜,但也不是留日派的铁杆;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健将,但和各派主事者若即若离;在旧党新派、左右两翼、朝野两端,他都有朋友,也都树论敌;晚年一度加入左联,随即公然决裂;上海十年是鲁迅声誉的顶峰,他的葬礼齐集了当时各路派别,可是他周围背后的现实势力,很简单,只他自己一个人,加上他的笔名。 近年有论者说,鲁迅没有主义、信仰,疏于现代国家的知识架构,不及英美派如胡适傅斯年等拥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现代理念。我同情这种说法,我也同意,鲁迅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苏联问题上,不及他的论敌看得清醒。但我从未在鲁迅那里期待英美式的宪政常识,鲁迅之为鲁迅,不在这一路。在民国言路的众声喧哗中,他不肯附和各种各样政治正确,总是成功地给大家一瓢冷水,一个扫兴,几句煞风景的话:因为他给出的不是政见,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义,他却来写一篇《药》,以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举事,他不过看成换了旗帜,唯一的赞扬,只是剪了辫子;北伐统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却震惊于清党的血腥;他晚年对红军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对延安方面的小党员说:你们成功了,进城了,我就要去扫大街,简直早就梦见了“文化大革命”……清末之际的西洋进化论,为最时髦,他怀疑而且讽刺,今天,中国人的整体人格整体素质,果然进化了吗?北洋时期的宪政闹剧,他也怀疑而且讽刺,且看如今年年两会的举手和图章,百年宪政的命运,昭然若揭;此外,二十年代关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争论,三十年代关于国防文学的争论,鲁迅的言说立场,均非正角;他或深或浅介入过当时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细留意,鲁迅,都不是某一话题、某一主张的确信者与肯定者,他要么审慎质疑,要么一句说破,要么反拨话头,要么娓娓辩难……我无法在此引述鲁迅的言论,总之,不要以为当年大家都在倾听并认同鲁迅,除了当权者,在民国各种舆论中,英美海归的自由主义阵营,第三势力的老少徒众,满嘴新词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势力大,都没停止过对他的批判和嘲骂,鲁迅的本钱,只一支笔,鲁迅的优势,只是很有名。 关于鲁迅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解读,各有道理,都是对鲁迅神话的有效解构,但在远为复杂的鲁迅那里,仍不免一纸标签、一顶帽子,或如鲁迅的比喻,成了一块“匾”。他的尖锐的怀疑,出于大爱大憎;他的浓黑的悲观的另一极,是游戏的天性,即胡兰成所谓“跌宕自喜”;他时常自称虚无,却委身实实在在的工作,嘲笑各种超然出世的高谈……我们很难在一个不变的立场上,观察鲁迅。他的难缠,他的醒豁,是在复杂感,并公开展示自己的冲突与矛盾,注意,不是见解的前后矛盾,而是精彩往来于事物的各个面向、各种可能。在几乎所有论题中,他的省思和意见出乎于各派观点之外,他的杂文总在曲折提醒道:事情并非如此,一切,比你们知道的还要复杂。 8. 这次因为匆忙,我给讲题起了很差的题目:想象鲁迅,既是起了,那就文章做下去,但不是“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 我知道这也是愚蠢的想象,但在其他地区,其他历史景观,譬如港台、日本、韩国,或者欧洲的鲁迅读者中,我隐约感知一位陌生的鲁迅——这位鲁迅没那么严重,没那么有名,绝不盖过所有名字,但他是一个可敬的麻烦,一直会在那里。阅读他,爱他的人,相当有限,相当边缘:早先台湾的鲁迅读者,绝对少数,这就有点对了;另有位小国(我忘记是哪个国家)的鲁迅读者说:“他是所有反抗者的朋友”,这就更对了。这些国家的鲁迅读者很难改变社会,更改变不了国家,但他们可能被鲁迅改变,变成小小的叛徒,至少,是敢于孤立的人。 所以请令飞兄原谅:?我在试图离开鲁迅被错置的地位,找回鲁迅的分量,以涉嫌贬抑鲁迅的方式,想象他的伟大。 前面说,鲁迅神话起于被政党的孤立;前面又说,鲁迅的真价值,是在异端。伟大的人物,十九异端,真的异端,总是孤立——请注意:不是“被孤立”——而伟大的孤立者,不幸,会使多数人不安,以至讨厌,以至规避:我看见,鲁迅是这样的命,也是这样的人。 鲁迅自己说,他是夜行的鸟,发出恶声:这是文学的修辞,也是大实话。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在相对完整而丰实的文明和历史中,鲁迅那样的恶鸟,不会获得他在现代中国这种吓人的地位,不该被膜拜,不该被恐惧,而是被尊敬,同时,被冷落。在人文思想领域,当然,这样的人享有无可替代的声名,被视为民族的传奇和荣耀,但一定不是唯一的形象,而是在至少三五个名字构成的不同维度间,闪烁稳定的光亮。虽然这位人物及其著作被几代人持续研究,但他可能从未被真的理解,从未停止被理解。可以确定的是:主流社会、主流价值,不会爱他、接受他。绝大部分人仅仅听说他的名字,不会读他,他属于一小撮人,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有没有这么一小撮人,这个国家会很不一样。 9. 许多年了,我总在其他历史人物中分神想象,窥视鲁迅的另一种境遇——譬如叔本华和尼采,其实德国公众不太理会他们;譬如伏尔泰或者萨特,法国公众也不太理会他们;去年是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俄罗斯报纸只给了次要页面,小小的纪念;三十年代被左翼和鲁迅相提并论的高尔基,如今在俄罗斯几乎是个被忘却的名字;索尔仁尼琴结束流放回到祖国,同胞不在乎他,年轻精英嘲骂他;美国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备受争议,从美国的语境看,攻击他的理由同样公正;苏珊·桑塔格逝世了,中国人凭着中国语境郑重追念她,但她在美国获得的认同,远非我们想象的普遍而重要……中国知识界想必熟悉类似的公案,好比法兰克福学派,好比结构主义群星,都是难缠的异端,天生的恶鸟,学贯古今,出语凶狠?。他们折腾一世,不是他们改变了什么,而是为了人的境遇,不惜诅咒国家。 这也是鲁迅的天性吗?以上人物不都是文学家,也未经历鲁迅的被通缉。鲁迅不如他们幸运,不是因为受迫害,而是智性与人格的寂寞,难逢对手,或者,对手的尺寸与智商,太不及他。他的风神与文采虽是那样的中国,却与转型期的现代中国,格格不入—他对历史的省思,他的非体系性,接近“重新评估一切”的尼采;他的辛辣与苦味,介于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他的仁厚与复杂感,接近托尔斯泰;他对同代文人的轻蔑,仿佛萨特—晚年的萨特说,他厌恶同龄人,只愿和晚辈,和女子交谈—但鲁迅同时兼有萨特的论敌,那位雷蒙·阿隆的特质,即对喧嚣甚上的政治正确,对一切慷慨激昂,时刻警惕。 鲁迅,年 但不论如何,鲁迅曾经活在以上人物的言论空间,在本土一流文人中,获得维度,凛然孤立。但他从未被置于欧美国家的文明景观,从未背衬一个公民社会—三十年代有位外国记者问他:贵国的阿Q最近怎样?鲁迅笑道:“哈!更糟,现在的阿Q已经当了国务委员!”晚年,除了家眷,真正给他放松与信赖的友人,是隔壁弄堂的日本老板。此后薄幸的论者,其中有林语堂,总说鲁迅多疑,乖僻,不好处,这是拿着俗世人情度量稀有的异端。这异端唯一一次与俗世妥协,唯一一次接受对于自己的肯定,就是他的葬礼,而鲁迅的被利用,认真说来,即肇始于那次庞大的送葬。到了年,鲁迅的凛然孤立,终止了,他从此进入历史的荒原,被单独抬举,同时,被彻底隔离。 年5月10日摄于上海内山寓所。左起:内山完造、内山夫人、高龟眉山、中村戒仙、鲁迅、铃木大拙、藤井草堂。 一个拒斥俗世的异端,在任一时代,为俗世的人群所厌弃,鲁迅,却被俗世膜拜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这庞大无边的俗世也和鲁迅一样,被政党全数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辈如胡兰成之流始得看清鲁迅的真价值:不是导师、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个叛徒,一个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国进入绝对肯定,不容叛徒的时代,这时代一路进步到今天,从未学得放松一点、放心一点,还比以往更经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轻微的叛变。可是大家看见:这样一种“现代文化”曾经留下极度乖张的一笔,是居然将一个超级的异端,奉为圣人。 年10月8日沙飞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鲁迅抱病出席活动,也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次影像。 10. 鲁迅很难回去了,这是无可挽回的灾难:我们和他一样,失去了容忍异端的生态,这短暂的生态与欧美相比,可怜之至,毕竟在三四十年代还曾像点样子,有点样子。我替鲁迅想念他的论敌,那些他侧目而轻蔑的人——近年,胡适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论现代国家的远大设想,现代文化的正当确立,以胡适而替代鲁迅的位置,其实倒是合宜,胡适和鲁迅同有耿介不让的一面,但与鲁迅的事事看破、预先绝望相对应,胡适即便在国府崩解、溃败南渡的时期,仍坚称自己是乐观的人。胡适的系统,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统,他终生容忍异见,与各种叛徒有私谊,但他的天性与实践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绅士,近于现代的国师。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先有蔡元培,后来有胡适之,是大可尊敬、应当纪念的两位开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绝对不敢竖一尊老校长胡适的小雕像—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化”怎么好意思说是“现代”,好意思说是“文化”。 但我乐意肯定今日中国莫名其妙的文化,毕竟,擅于权谋和机变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D文化也还审时度势,释放鲁迅,默认胡适及一大群反动派,带着他们的著作,回到阳世。在眼下的经济丰年与文化荒原之间,我们仍在纪念文化叛徒周树人,多少有点超现实,但鲁迅知道,不会诧怪:他早就预见日后中国的大荒凉,只怕他料不到文化的荒原变得这么有钱。 请容我再说一遍:这就是我大肆误解的“中国现代文化”。接下来,我愿为这份光芒万丈的文化光荣榜,唱一道名单——首先,是历届党国元首,其次,是千千万万共和国烈士,再次,当然,应该是钱学森杨振宁他们—这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防科委中国航天部等等等等机构人员的漫长名单,请原谅,我实在背不齐全—再再次,必须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刘翔,兼带所有奥运金牌银牌的获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缤纷的CCTV春晚舞台大阵容,主持人两端,站着我们的赵本山与小沈阳。 最后,请诸位说说看,鲁迅先生该不该列入中国现代文化的这份光荣榜? 年3月17日写在北京 本文选自陈丹青《草草集》 有删节,完整文章请阅读书籍 长按-扫描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好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新闻丨上海行俱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约,顺
- 下一篇文章: 上海建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校友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