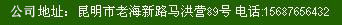|
作者:傅国涌 从年到年,年轻的范长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在中国新闻界大放光彩,但最后只落得自杀的下场。年10月脱离《大公报》之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新闻记者。 范长江为什么离开《大公报》?年1月(即他生命结束前一年),他本人在“交代材料”中说是因为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社论稿,与张季鸾发生分歧,“我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并牵扯到年秋天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称自己的这篇文章就是“反对上述‘三个一’的反动纲领,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张季鸾扣发这篇稿子,他就拿到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原文发表,张更加恼怒。随后胡政之找他谈话,要他放弃拥护中共的态度,他说:“我不能改变我的政治态度,我也不能再在《大公报》工作。”言下之意,他离开《大公报》完全是因为政治分歧,是与《大公报》“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的说法只是一面之词,何况写于“文革”期间,可信度不高,起码在时间上就不吻合,《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写于年1月,而蒋介石的“三个一”是秋天提出的;他的文章一月份所写,发表于《抗战三日刊》,而他离开《大公报》是这年十月,显然这不是导致他离开的直接原因。他所说的并不是实情。 年2月他开始于的延安之行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当时范长江希望留在陕北,毛泽东则劝他回到《大公报》去,认为他留在《大公报》作用更大,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共的政策。 毛泽东与范长江 年2月14日,他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接着他在《国闻周报》发表《陕北之行》的连载,毛泽东欣喜万分,3月29日亲笔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 年3月29日,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年的范长江已是名满全国的大记者,他的新闻通讯风行一时,享有极高的声誉,拥有众多读者、崇拜者,他的自负、“舍我其谁”心态都可以理解。《大公报》对他也是另眼相看,年4月,他从前线采访绕道汉口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张季鸾亲自主持宴会为他洗尘。爱才如命的胡政之、张季鸾想把他培养成合格的报人完全在情理之中。即使到了年,从范长江的交代材料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胡、张给他提供的舞台,对他的器重和宽容,以及《大公报》对民间独立性的真诚追求── “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 这番回忆生动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年范长江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说的恐怕更接近真实:“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而我个人则因此遭受某些人特殊的关顾,信件来往检查特严。” 其中并没有提及胡政之“动摇过几次”,这些文字写于年,离年不过三年,而范长江的笔端依然胡充满敬意,没有丝毫的怨言。 徐铸成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张季鸾曾告诉他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我叫他学写社评,他不满有些稿子给人删改,后来他和某人已积不相容,根据报馆章程,只能忍痛让他走了。”这“某人”显然是指王芸生。但这只是一个孤证,经不起事实推敲,比如说删改文章,年范长江本人的“交代材料”里也说没有这事,“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社欢迎战地记者时的合影﹙前排右一为范长江﹚ 年后去了台湾的陈纪滢回忆,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作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孔昭恺回忆:“据说他向张先生要求编报,他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第二天范长江就离开了《大公报》,“到底为了什么?对我一直是个谜。” 两人的说法基本吻合,可以相互印证。两个亲历者的记忆或许有不尽准确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还有个人原因,是他意气用事的结果。方蒙在《范长江传》中虽然说他离开《大公报》是政治原因,但也说他不耐烦上夜班。他仓促离开《大公报》,周恩来深感惋惜和痛心,对于讲究实际的领袖来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远没有留下的价值大。所以周才会亲自找徐盈、子冈等谈话,要他们安心留在《大公报》,“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 范长江的离开,对于《大公报》也是一个损失,以兼容并包、无党无派、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记者的《大公报》不是容不下一个左倾的范长江,年《大公报》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身份泄露,胡政之还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并兼任驻日记者。早在年3月,范长江就参与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组织,《大公报》不会不知道。要说他仅仅因政治分歧脱离《大公报》,那也不可能拖到这一年十月。 范长江在《大公报》前后只有四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一生的总和,他奉献给世人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战地通讯都已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他的《中国的西北角》白癜风怎样治中科白癜风医院微博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中国新闻出版报刊发报道海媒股份叩响资本
- 下一篇文章: 一份报纸的死亡引发的集体忧伤观察